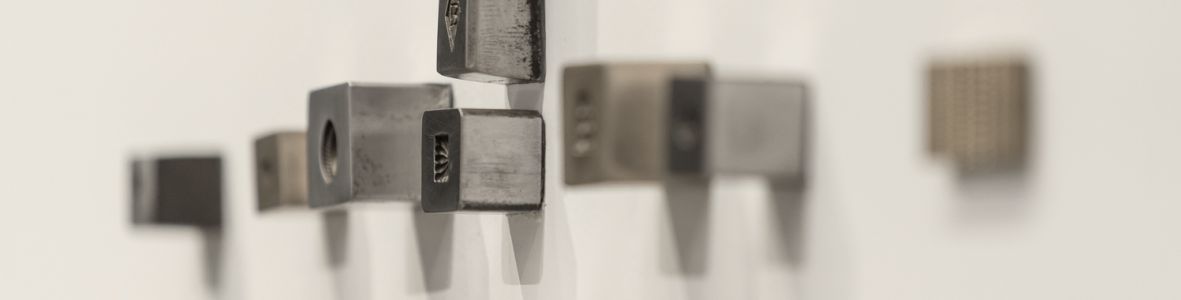本文原载于一筑一事
发表时间:2018-10-29
艺术是一个途径
一个让你脱离
琐碎的、日常的、机械的
生活现实的途径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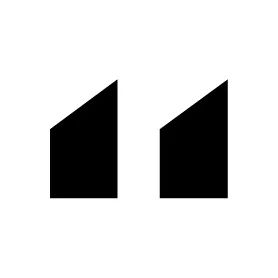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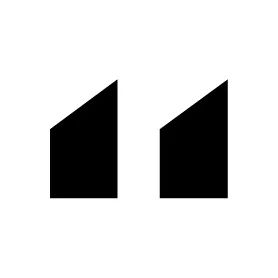
蓬皮杜
它是不知道成都的
在这次展览之前,蓬皮杜工作人员、包括宁琤,没有人来过成都。
成都是什么?牛王庙搓麻将的本地嬢嬢无法定义,艺术家兼春熙路“gai娃”的王亥也无法定义。
在此短居数月,宁琤也仅仅有了些感觉,“有时候觉得这儿像加利福尼亚,有特别多可塑性,却也有自身的节奏感”。


而当宁琤在聊天中陆续提及汪建伟、张晓刚、何多苓、肖全、邱黯雄、刘家琨、唐蕾这一串名字的时候,我方才突然意识到——
“哦,中国最重要的一批当代艺术家,似乎都是从成都走出去的”。
这也是蓬皮杜落地成都的重要因素。

1982年,何多苓、张晓刚、周春芽于川美毕业,一帮艺术家挤居在玉林“沙子堰”——以艺术的名义,摇滚、喝酒、谈一夜人生海海。
此时何多苓画下《春风已苏醒》,这幅画后来被称为“中国伤痕美术”的代表作。

1984年,肖全复员回到成都,他拍下九眼桥的自行车大军,拍下青石桥的茶客,也拍下文殊院外的“超妹儿”……
后来,他被称为“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”。
张晓刚和唐蕾的小酒馆诞生在1997年。沈晓彤取了“小酒馆”这个名字,邱黯雄绘制了沿用至今的那只手的LOGO,而刘家琨则设计了小酒馆的外观。
赵雷一首《成都》唱红了小酒馆,少有人知道的是,当年就在小酒馆附近,何多苓和瞿永明还合伙开了一家“白夜酒吧”。



建筑、绘画、音乐…… 甚至是现代教育(川大比北大还早2年建校),“当代成都”似乎的确在文化艺术领域有自己的章法。
对于这场即将开幕的“全球都市#1.5”,宁琤浑身的细胞都充满兴奋感。
她将这次展览形容为“A Festival”,而且“远胜于巴黎”。

当巴黎展在美术馆等艺术机构中探头探脑,今年在成都,城市就是展场。
从锦城湖到东郊记忆,从活水公园到夹江县,艺术家与其装置以散点,跨界、打散于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库勒·阿基米德(Kunlé Adeyemi)因蓬皮杜之邀,几个月前第一次来了成都——一老外,一来就扎进望江公园的老茶馆。

“这帮老外,可忙坏基金会陪同翻译的孩子们了”,宁琤又开心又心疼。
库勒的作品原本是漂浮学校(Floating School),获得威尼斯双年展,原为应对非洲Makoko沿海气候变化而设计——“但自打这家伙跟茶馆儿那老太太一聊天,好家伙,开始研究起岷江水上生活形态了”。
某种意义上,借这次双年展的机会,艺术家与成都这座城市互相启发着彼此。

在夹江石堰村,毛继鸿基金会另一组翻译小分队,已陪艺术家驻扎一月有余。
“第一个小组刚回,第二个小组又去了。”
志愿者被要求骑自行车,像当地人一样赶集,观察老年人的生活习惯。虽然语言不通,当地村民与这群老外却互相瞧着“有意思”。

村子没有像城市咖啡馆、广场一样的空间,所以当艺术家要找村民聊天的时候,几条长凳一凑,便成为“不存在的、可移动的、可创造的”公共空间。
“他们拍回来的照片儿,有时候一条凳上一水老头儿,有时候又能男的和女的坐。这就是农村文化里人和人的关系。”


夹江项目大家给它取名为“留”,留下的留。艺术家希望村子这种“非物质文化”,不能说遗产,文化能留下来。
这种与村民共建的模式——艺术家突破原来固有的“城市圈”,将自身哥伦比亚、印度尼西亚背景下的建筑与音乐,带入甚至你我都未曾到访的成都夹江县石堰村——同样是艺术。
不止是茶馆、乡村,甚至成都的小学生们都与蓬皮杜进行过5次“深度合作”了。

澳大利亚艺术家组合阿尔弗雷德和伊莎贝尔·阿奎礼赞(Alfredo and Isabel Aquilizan)为本次展览所设计的大型装置《居所:他乡计划》,邀请大量的成都学生、家庭、居民等共同参与到构想之中。
宁琤带我参观布展现场,成都小学生们对“房子”的构想就在眼前了——别墅带蓝色泳池,“Fridens Only”的树屋塔楼,还有一栋左半边房顶属于“中国解放军”、右半边属于“刺激战场”的川西结构院落。
她半开玩笑地说,“你看京东的logo是不是太多了?”


互动、跨界、艺术、居民,这样一场展览,哪怕在巴黎、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亦是前沿而新鲜的。
我不禁好奇,“您觉得成都人能接受吗?”
宁琤两手一摊,“不知道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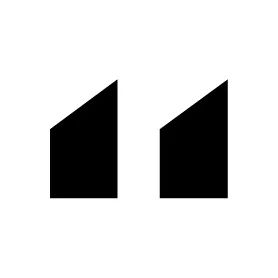
左岸咖啡与麻辣烫
这些日子以来,宁琤这位“首席执行官”每天都跟做花样体操一样。
虽由巴黎直接策展,但落地执行的担子全压在了毛继鸿基金会的身上——就连东郊记忆布展现场的工人,都是从上海来的。
宁琤掏出手机日程表给我看,从采访当天到开幕式再到明年一月,蓝的红的紫的——而她竟然还在这满当当的日程之中,偷摸观察成都人。

“成都人敢生活。意思是他对生活有要求。不是住在什么地方、养什么花儿,这种简单层次,而是我活了一辈子,要活出精彩。”
“这个东西,使成都人特别个性化。”
这让我想起祥和里的蟹蟹大排档,老板很歪,不接受预约,“斗是我妈来,也要排队”;也想起小牛锑锅串串,“每晚酒尽人散数完签签,这个串串店老板就趴在桌上写起人生”……
宁琤暂时还没空在成都走街串巷,与麻辣烫和锅巴土豆也不熟,但她熟悉巴黎人的夜生活,展览、剧场、音乐会——哪怕30人的剧场,都是爆满。

结合自身的工作状况,我惊讶于巴黎人充裕的“业余时间”。
“他们不加班吗?”“也加班。但他们的加班跟我们的状态不太一样。”
全世界的速度都在加快,巴黎也是,“但是巴黎人有这样一个习惯,剧院、音乐、电影,能让他们抵抗这种加速的裹挟。”

不自觉地,我脑子里升腾起一条交叉的时空线:成都火锅串串店门口排起的长队、茶馆里乒铃乓啷的麻将,巴黎艺术中心与博物馆门口的长队、咖啡厅雷打不动一日三杯花神咖啡的日常……
或许这就是我们抵抗平庸日常的方式。
像宁琤说的,“成都有时差”。
不是说它不时髦、不艺术、不好,而是这座城市正循着自己的节奏与逻辑在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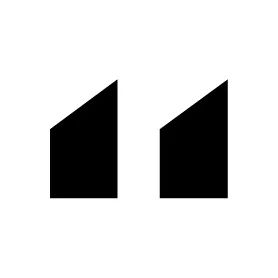
后记
从I.T.United中国区执行副总裁,到蓬皮杜展览落地执行人,宁琤给我讲了一个医院的故事。
“你生病在医院,早上5点爬起来,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下,就要拿着小板凳去排队。”
“你看着那么多的人,你不认为科技真正能彻底改变人的生存的状态,而我以前认为科技是可以拯救世界的。”
于是当有一天,宁琤获得一个停下来的契机——她毫不犹豫地,停了下来。
END